自從他們在我大學時因為意外去世後,這裡就一直空著。
我打開門,一股塵封已久的氣味撲面而來。
屋子裡的陳設,還維持著他們離開時的樣子。
牆上掛著我們一家三口的照片。
照片上,我笑得燦爛,父母慈愛地看著我。
那時候的我,還不知道,未來的生活,會有那麼多的苦難和波折。
我伸出手,輕輕地拂去相框上的灰塵。
指尖觸碰到父母的笑臉,冰冰涼涼。
眼淚毫無預兆地掉了下來。
爸爸,媽媽。
對不起。
我沒有把自己照顧好。
我很快就要來陪你們了。
你們會怪我嗎?
我在老房子裡待了一個下午。
把屋子裡的角角落落都重新打掃了一遍。
傍晚的時候,我坐在院子裡的鞦韆上,看著夕陽一點點落下。
就像在看我的人生緩緩落幕。
手機響了起來,是一個陌生的號碼。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了。
電話那頭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帶著哭腔,歇斯底里。
「林殊!你這個賤人!你到底跟司硯說了什麼?」
是江暖。
聽著她在電話那頭氣急敗壞地咒罵,我竟然覺得有些好笑。
「我說什麼,重要嗎?」我淡淡地反問。
「重要的是,傅司硯信了什麼。」
「你……」江暖被我噎得說不出話來,「林殊,你別得意!司硯他愛的人是我!他只是暫時被你蒙蔽了!等他清醒過來,你什麼都不是!」
「是嗎?」我輕笑一聲。
「那你就慢慢等吧。」
「等你從監獄裡出來,看看他還在不在原地等你。」
說完,我便掛了電話。
我不想再和她多說一句廢話。
和一個活在自己幻想里的人爭論,毫無意義。
天,徹底黑了。
院子裡沒有開燈,四周一片漆黑。
我坐在黑暗裡,卻感覺無比心安。
或許,我就該屬於黑暗。
就在我準備起身回屋的時候。
院子門口傳來了一陣輕微的響動。
緊接著,一個人影推開了那扇虛掩的門,走了進來。
他沒有出聲,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
但我知道,是他。
是傅司硯。
他身上的冷木香,隔著那麼遠都那麼清晰。
他就像一個幽靈,無論我逃到哪裡,他都能找到我。
9
傅司硯就站在院門口,沒有再往前走一步。
我們之間,隔著半個院子的黑暗。
誰也沒有說話,只有晚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
這種對峙,讓我覺得很累。
「你來幹什麼?」最終,還是我先打破了沉默。
「你的律師聯繫我了。」他的聲音在夜色里,顯得有些飄忽,「關於財產捐贈的事。」
原來是這樣。
我自嘲地勾了勾唇角。
他大概是覺得,我連死都要算計他一把,用他的錢去做善事,博一個好名聲。
「那是我自己的錢,我想怎麼處理是我的自由。」我冷冷地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急忙解釋道,聲音里透著一絲慌亂。
「林殊,我知道,無論我現在說什麼,你都不會信。」
「但我還是想說。」
「錢,我可以捐。傅氏集團,我也可以捐。」
「我什麼都可以不要。」
「我只要你。」
他說得那麼懇切,那麼卑微。
如果換作是別的女人,聽到一個男人願意為自己放棄整個商業帝國,大概會感動得一塌糊塗吧。
可我,只覺得可悲。
我和他,已經走到了要用「捐贈整個集團」來證明愛的地步了嗎?
這場愛情,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算計和交易。
現在,連挽回,都帶著一股金錢的銅臭味。
「傅司硯,」我從鞦韆上站起來,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他走過去。
我的視力,在夜晚,變得更差了。
我幾乎看不清他的臉,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輪廓。
我在離他三步遠的地方停了下來。
「你是不是覺得,你擁有的一切,金錢、地位、權勢,可以買到世界上任何東西?」
「包括我的原諒?」
他沒有說話,算是默認了。
我笑了,笑聲在寂靜的夜裡顯得格外清晰,也格外淒涼。
「你錯了。」
「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是你永遠都買不回來的。」
「比如,時間。」
「比如,信任。」
「比如,一個被你親手傷透了心的人。」
我的話,像一把鈍刀,一下一下地割在他的心上。
我能感覺到,他呼吸的節奏亂了。
「林殊……」他艱難地開口,聲音裡帶著濃重的鼻音,「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混帳事。」
「是我瞎了眼,是我被豬油蒙了心。」
「你打我,罵我,怎麼樣都行。」
「只求你,別用這種方式懲罰我。」
懲罰?
我從未想過要懲罰誰。
我只是想,在我生命的最後階段,能活得像個人樣。
而不是一個被他囚禁在金絲籠里的,沒有靈魂的娃娃。
「我沒有懲罰你。」我平靜地說,「我只是在,放過我自己。」
「傅司硯,你也放過我吧。」
「算我求你了。」
我說出「求你」兩個字的時候,感覺自己所有的力氣都被抽空了。
對這個男人,我真的再也沒有任何期待了。
我的示弱,似乎比任何強硬的拒絕都更能擊潰他。
他高大的身軀,在夜色里,劇烈地顫抖著。
我聽到了一聲壓抑到了極點的、類似於嗚咽的聲音。
我認識傅司硯這麼多年,從未見過他哭。
他永遠都是那麼驕傲,那麼不可一世。
仿佛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事,能讓他低頭。
可現在,他為我哭了。
可惜,我看不見。
也不想看見。
我繞過他,走出了院子。
我沒有回頭,也沒有停下腳步。
我怕我一回頭就會心軟。
我怕我一停下,就再也走不掉了。
身後,傳來了他撕心裂肺的喊聲,一遍又一遍地叫著我的名字。
「林殊!」
「林殊!」
「林殊……」
聲音,最終被我關在了身後那條長長的、黑暗的巷子裡。
我走在燈火通明的大街上,身邊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可我的世界,卻只剩下無邊無際的寂靜和寒冷。
10
手術的前一天,我搬進了醫院。
一間單人病房,乾淨又安靜。
王醫生來看過我,告訴我手術的準備工作已經全部就緒。
「林小姐,放輕鬆,傅先生請來了世界上最好的眼科專家團隊。」他安慰我。
我扯了扯嘴角,算是笑了一下。
又是傅司硯。
這個男人,就像一張無形的大網,把我困在其中,讓我無處可逃。
我沒有拒絕他安排的這一切。
因為我知道,拒絕也沒用。
更重要的是,我想活下去。
哪怕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希望,我也想試試。
我想看看,沒有傅司硯的世界,會是什麼樣的。
辦理住院手續的時候,律師朋友來看我。
她給我帶來了一束向日葵,燦爛得像太陽。
「醫生說,你現在對光線很敏感,不能看太刺激的顏色。」她把花放在離我稍遠一點的柜子上,「但這花,寓意好。向陽而生。」
我笑了笑,「謝謝。」
她在我床邊坐下,握住我的手。
她的手心很溫暖。
「都安排好了?」我問。
她點了點頭,「嗯。離婚手續,財產捐贈協議,都辦妥了。」
「傅司硯那邊,沒有阻攔?」
「他……」律師朋友的表情有些一言難盡,「他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三天三夜了。誰也不見。」
「公司的幾個大項目,都停了。」
「我去找他簽字的時候,他整個人……瘦了一大圈,鬍子拉碴的,跟個流浪漢一樣。」
「他把所有的文件都簽了,一句話都沒說。」
「只是最後,他問我,『她還願意見我嗎?』」
聽到這些,我的心竟沒有一絲波瀾。
或許是真的死了吧。
「你怎麼說的?」我問。
「我說,『傅先生,您覺得呢?』」律師朋友學著我平時的語氣,惟妙惟肖。
我被她逗笑了。
「乾得漂亮。」
我們倆相視一笑,病房裡的氣氛也輕鬆了不少。
她陪我聊了很久,聊我們大學時的趣事,聊我們對未來的幻想。
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未來會像我們想像中那樣,美好又燦爛。
卻沒想到,生活遠比戲劇更狗血。
送走律師後,病房裡又恢復了安靜。
我躺在床上,閉著眼睛,感受著生命一點一點地流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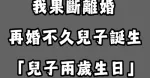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