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過了多久,病房的門被輕輕地推開了。
我以為是護士,沒有睜眼。
腳步聲,很輕,很慢,一步一步地,朝我的病床走來。
然後,在我的床邊停了下來。
我聞到了一股熟悉的冷木香。
我的身體瞬間僵住了。
是他。
傅司硯。
他還是來了。
我沒有動,繼續裝睡。
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
也不知道他想幹什麼。
他就在我床邊,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幾乎以為他會一直站到天亮。
然後,我感覺到,一滴溫熱的液體,滴在了我的手背上。
緊接著,是第二滴、第三滴……
是他的眼淚。
他竟然又哭了。
我的心,像被針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
最終,我還是沒忍住,睜開了眼睛。
月光從窗戶里灑進來,照亮了他那張憔悴的臉。
他的眼睛紅得像兔子。
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他看到我醒了,像是被嚇到了一樣,慌忙地伸手去擦眼淚。
那副手足無措的樣子,狼狽又可笑。
「我……我吵醒你了?」他聲音沙啞,帶著濃重的鼻音。
我沒有回答他,只是靜靜地看著他。
「我……我就是想來看看你。」他語無倫次地解釋著,「我保證,我不會打擾你。我就在外面……看著你。」
我還是沒有說話。
我的沉默讓他更加不安。
他看著我,眼神里充滿了哀求和恐懼。
仿佛我是那個隨時會宣判他死刑的法官。
「林殊,」他終於忍不住,在我床邊蹲了下來,仰起頭看我。
這個曾經那麼高傲的男人,此刻卻卑微到了塵埃里。
「我看了你所有的檢查報告。」
「我諮詢了所有的專家。」
「我知道,那場車禍給你帶來了多大的傷害。」
「我也知道,這三年你是怎麼一個人熬過來的。」
「對不起,對不起……」
他不停地重複著這三個字,聲音裡帶著無盡的悔恨和痛苦。
他伸出手,想要觸碰我,卻又在半空中膽怯地收了回去。
「我還能……為你做點什麼?」他問,聲音裡帶著一絲顫抖的希冀。
「什麼都好。」
我看著他,看著這個我曾經愛到骨子裡的男人。
突然覺得,一切都像一場荒誕的夢。
「傅司硯,」我緩緩開口,聲音平靜得像一潭死水。
「你現在做的這一切,是出於愧疚,還是愛?」
11
我的問題,像一把鋒利的刀,直直地插進了傅司硯的心臟。
他蹲在那裡,整個人都僵住了。
臉上的悲傷和悔恨,瞬間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迷茫。
是啊。
是愧疚,還是愛?
或許,連他自己,都分不清楚。
他對我的好,對我的挽留,究竟是因為虧欠,還是因為,他終於後知後覺地發現,他愛上了我這個,他曾經最不屑一顧的女人?
見他遲遲不回答,我心中最後一點微弱的火苗,也徹底熄滅了。
果然。
他根本不愛我。
他只是無法接受,自己犯下的,不可饒恕的錯誤。
他只是無法承受這份沉重的、足以壓垮他的愧疚感。
我閉上眼睛,感覺一陣深深的疲憊。
「你走吧。」我說。
「我累了,想休息。」
我的聲音很輕,卻帶著不容置喙的決絕。
「林殊……」他似乎還想說什麼。
「走。」我加重了語氣。
我不想再看到他。
不想再聽他說那些毫無意義的廢話。
病房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我能感覺到他的視線,像烙鐵一樣燙在我的臉上。
過了很久,我聽到了一聲極力壓抑著的、痛苦的抽氣聲。
然後,是腳步聲。
他站了起來,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我的病房。
門被輕輕地帶上。
整個世界都安靜了。
我睜開眼睛,看著慘白的天花板。
眼淚,終於還是不爭氣地流了下來。
林殊啊林殊。
你還在期待什麼呢?
這個男人,從來就沒有愛過你啊。
你為什麼就是不肯死心呢?
那一夜,我徹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被推進了手術室。
冰冷的無影燈,照得我睜不開眼。
麻藥,一點一點地注入我的身體。
我的意識開始變得模糊。
在徹底失去知覺前,我的腦海里閃過的最後一個畫面。
不是傅司硯那張悔恨交加的臉。
而是三年前的那個雨夜。
在刺耳的剎車聲和劇烈的撞擊中,我毫不猶豫地撲向了他。
用我單薄的身體,為他築起了一道生命的屏障。
那時候,我只有一個念頭。
他不能死。
只要他活著,我怎麼樣都無所謂。
原來,愛一個人,真的可以奮不顧身到這種地步。
只是,我的這場奮不顧身……
最終,感動了自己,卻成全了一場天大的笑話。
……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像是在一個漫長又黑暗的隧道里不停地穿行。
沒有盡頭,也沒有光明。
直到有一天,我聽到耳邊,傳來了一陣陣,熟悉的,海浪聲。
還有,一個男人,低沉又沙啞的聲音。
他在給我講故事。
講安徒生童話。
講海的女兒,講賣火柴的小女孩。
每一個故事的結局都是悲劇。
聲音很溫柔,卻透著一股化不開的悲傷。
我努力地想要睜開眼睛。
眼皮卻像有千斤重。
我動了動手指,想要告訴他我聽到了。
可我卻使不出一絲力氣。
我是死了嗎?
這裡,是天堂,還是地獄?
為什麼,我還會聽到傅司硯的聲音?
12
不知過了多久,我終於在一個清晨醒了過來。
眼前,不再是一片黑暗。
而是一片朦朧的白。
像隔著一層厚厚的毛玻璃,能感覺到光,卻看不清任何東西。
我的眼睛上蒙著厚厚的紗布。
我抬起手,想要把它摘下來。
一隻溫暖的大手卻輕輕地握住了我的手。
「別動。」
是傅司硯的聲音。
他的聲音,比我昏迷前,聽到的,更加沙啞了。
像被砂紙反覆打磨過一樣。
我沒有再動,任由他握著我的手。
我能感覺到,他的手心布滿了粗糙的薄繭。
這不像那個養尊處優的傅家大少爺的手。
「手術……成功了嗎?」我開口,聲音乾澀得厲害。
「成功了。」他回答得很快,語氣裡帶著一絲難以掩飾的喜悅。
「王醫生說,你的視神經恢復得很好。再過一周,就可以拆紗布了。」
是嗎?
我竟然還能重見光明。
老天爺,終究還是沒有對我太殘忍。
我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感受著失而復得的希望。
病房裡很安靜,只有我們兩個人的呼吸聲。
還有窗外,傳來的,海浪的聲音。
「這裡是……?」我問。
「是一家私人療養院。」他說,「在海邊。這裡的空氣好,適合你休養。」
又是他的安排。
我心裡五味雜陳。
「你一直都在這裡?」我問。
「嗯。」他應了一聲,握著我的手又緊了緊。
「我怕你醒來看不到我。」
他的話讓我心裡一顫。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只能選擇沉默。
接下來的日子,傅司硯幾乎是寸步不離地守著我。
他親自給我喂飯、擦身、讀報紙。
甚至在我起夜的時候,他都會像抱一個孩子一樣,把我抱到衛生間。
他做得那麼自然,那麼熟練。
仿佛已經做過千百遍。
我沒有拒絕,也沒有回應。
我就像一個沒有感情的木偶,任由他擺布。
我只是,還沒想好,該如何面對他。
也還沒想好,該如何面對,我們這段,千瘡百孔的關係。
拆紗布的那天,天氣很好。
陽光,透過窗戶,灑進病房裡,暖洋洋的。
王醫生、傅司硯,還有我的律師朋友都來了。
當王醫生,一層一層地,解開我眼前的紗布時。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最後一層紗布被揭開。
我慢慢地、慢慢地睜開了眼睛。
一束刺眼的光射了進來。
我不適應地眯起了眼。
過了好一會兒,我才終於看清了眼前的世界。
很清晰。
比我生病前的任何時候都要清晰。
我看到了,窗外那片,蔚藍的大海。
看到了,床頭柜上那束,燦爛的向日葵。
也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傅司硯。
他瘦了好多,也黑了好多。
眼窩深陷,下巴上還帶著來不及剃掉的胡茬。
整個人,都透著一股,滄桑和疲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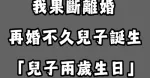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