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傅司硯提離婚那天,他正在給他白月光剝蝦。
冰冷的蝦殼丟進我面前的⻣碟,堆成⼀座⼩山。
他眼⽪都沒抬,像打發一個乞丐:「林殊,別鬧了,這個月的生活費已經打給你了。」
我沒接話,只是把一份簽好字的協議推過去。
直到他看見「離婚協議」四個字,才終於捨得從他⼼上人⾝上挪開視線,落在我⾝上,眼神冰冷⼜譏諷。
「可以,」他輕飄飄地說,「但你凈⾝出戶。」
我卻笑了,告訴他:「我要⼀千萬。現金,明天之內到帳。否則,我們法庭見。」
他大概以為我瘋了,但我知道,他會給。
1
傅司硯的錢,很快就到帳了。
整整⼀千萬,⼀分不多,一分不少。
就像是我們這三年婚姻的絕筆遣散費,冷冰冰的,帶著十⾜的羞辱。
我的律師朋友都覺得我瘋了。
放著傅家少奶奶的身份不要,放棄分割那天文數字般的夫妻共同財產,只要這一千萬。
「林殊,你是不是有什麼把柄在他手上?」律師問得⼩心翼翼。
我搖了搖頭,手指在冰涼的桌面上輕輕划過。
把柄?
或許吧。
我唯⼀的把柄,就是我愛他。
⽽這,是他永遠都不需要知道的秘密。
拿到錢的第二天,我做的第⼀件事就是去了醫院。
不是為了看病,而是為了預約一場手術。
一場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三十的手術。
當我拿著一沓厚厚的檢查報告走出醫院時,陽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抬手擋在眼前,世界在我的視野里只剩下模糊的光暈和色塊。
就像一幅被打翻了顏料的油畫,濃烈,卻看不真切。
身後傳來刺耳的剎車聲。
一輛黑色的賓利停在我身邊,車窗降下,露出傅司硯那張英俊卻毫無溫度的臉。
他大概是來確認我是否履行承諾,滾出他的世界。
「上車。」他命令道。
我沒有動。
他耐性告罄,推門下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氣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頭。
「林殊,你又在玩什麼把戲?」
他的聲音里充滿了不耐和猜疑,仿佛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處心積慮的表演。
我掙開他,從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遞給他。
不是離婚協議,也不是財產證明。
而是一份人體器官捐獻志願書。
他愣住了,視線落在文件上,眉頭緊緊皺起。
「你什麼意思?」
我笑了笑,只是覺得有些累。
我慢慢地,一字一句地告訴他:「傅司硯,沒什麼意思。」
「只是我的眼角膜,簽了死後捐獻。」
「想著你那位白月光江暖小姐,不是一直覺得眼睛不夠漂亮嗎?」
「我的,或許她能用得上。」
2
傅司硯的臉色在那一瞬間變得極其難看。
他死死地盯著我,像是要從我平靜的臉上,找出哪怕一絲一毫撒謊的痕跡。
可他失敗了。
我太鎮定了,鎮定得不像一個即將失去光明,甚至可能死在手術台上的人。
「林殊,收起你這套可笑的把戲。」他從牙縫裡擠出這句話,伸手就要來奪我手裡的捐獻志願書。
我卻先一步將它收回了包里。
風吹起我的頭髮,有些散亂地貼在臉頰上。
我能感覺到他的視線,像手術刀一樣,在我臉上凌遲。
結婚三年,他從未這樣看過我。
他看我的眼神,要麼是像看一件家具那樣漠然,要麼是像看一個麻煩那樣厭煩。
唯獨沒有此刻的驚疑和探究。
「傅司硯,你覺得我在演戲?」我輕聲問,語氣裡帶著一絲自己都未察覺的疲憊。
「難道不是嗎?」他冷笑,「為了錢,你什麼事做不出來?先是要一千萬,現在又拿眼角膜來噁心我,下一個劇本是什麼?絕症通知書?」
他的話像淬了毒的刀子,刀刀見血。
是啊,在他眼裡,我林殊就是一個為了錢不擇手段的女人。
三年前,他爺爺病危,需要一場商業聯姻來穩定傅家的股價和人心。
而被選中的我,就像貨架上的商品,被明碼標價。
我拿了錢,嫁給他,扮演一個聽話溫順的傅太太。
我們之間,本就是一場交易。
怪只怪我,不小心動了心,輸得一敗塗地。
世界在我眼中,又開始模糊起來。
我眨了眨乾澀的眼睛,努力讓視野變得清晰一些,但效果甚微。
我知道,我的時間不多了。
我不想再和他耗下去。
「信不信由你。」我轉過身,準備攔一輛計程車。
手腕卻再一次被他攥住。
這一次,他的力道里,竟帶了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
「你要去哪裡?」
「不關你的事。」
「林殊!」他幾乎是吼了出來,引得路人紛紛側目。
我煩躁地皺起眉。
這樣的糾纏,是我最不想要的結局。
我想要的,是安安靜靜地離開,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不留任何痕跡。
我用力甩開他的手,但失敗了。
他把我拽向他的車,粗暴地將我塞了進去。
車門落鎖,隔絕了外界的一切。
狹小的空間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壓抑的呼吸聲。
他發動了車子,沒有問我去哪兒,只是一路疾馳。
我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街景,那些原本熟悉的建築和招牌,在我眼中都變成了一團團扭曲的光影。
我忽然覺得很好笑。
這場鬧劇,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收場?
車子最終停在了一家私人醫院門口。
傅司硯把我從車裡拖出來,直奔頂樓的 VIP 病房區。
他把我甩在一個醫生面前,指著我說:「給她做個全面檢查,尤其是眼睛。」
那位白髮蒼蒼的老醫生,看到我時,眼神里流露出一絲驚訝和惋惜。
他扶了扶眼鏡,對傅司硯說:「傅先生,林小姐的病,不是儀器能檢查出來的。」
「她的病,在心裡。」
3
「心裡?」傅司硯重複著這兩個字,眼神里的嘲諷幾乎要溢出來。
他看向我,像在看一個天大的笑話。
「你的意思是,她裝病?」
老醫生姓王,是國內腦科的權威,也是傅家的家庭醫生。
他看著我,嘆了口氣,沒有直接回答傅司硯的問題。
而是對我說:「林小姐,你最近是不是視野缺損越來越嚴重了?頭痛和眩暈的頻率也更高了?」
我點了點頭。
「是。」
「上周給您開的藥,還有在按時吃嗎?」
「嗯。」
傅司硯的臉色越來越沉,他顯然失去了所有耐心。
「王伯,我沒時間在這裡聽你們打啞謎。」他語氣強硬,「我只想知道,她的眼睛到底有沒有問題。」
王醫生沉默了片刻。
他摘下眼鏡,慢慢擦拭著,然後才重新看向傅司硯,目光複雜。
「司硯,你還記得三年前那場車禍嗎?」
車禍。
這兩個字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傅司硯記憶的閘門。
我看到他的身體微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
他的眼神也變了,從剛才的譏諷和不耐,變成了一種深不見底的晦暗。
三年前,我們剛結婚不到一個月。
在一個雨夜,他開車帶我回老宅吃飯。
路上,一輛失控的貨車迎面撞了過來。
在碰撞發生的瞬間,我幾乎是憑著本能撲過去護住了他。
後來,他只是輕微的腦震盪,而我顱內出血,昏迷了三天三夜。
所有人都說我命大。
只有我自己知道,從那場車禍醒來後,我的世界就和以前不一樣了。
我的右眼,開始出現間歇性的失明。
視野里,總有一塊抹不掉的陰影。
我告訴過傅司硯,但他說什麼來著?
哦,他說:「林殊,苦肉計演一次就夠了,演多了,就沒意思了。」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提過。
我一個人去看醫生,一個人做檢查,一個人面對著眼前世界一點點被黑暗吞噬的恐懼。
而他,正忙著安撫他受了驚嚇的白月光江暖。
據說,江暖因為目睹了車禍現場,嚇得好幾天都做噩夢。
真是可笑。
一個害人者,卻成了最需要被呵護的受害者。
見傅司硯不說話,王醫生繼續說道:「那場車禍,林小姐的顱內有淤血壓迫到了視神經。這三年來,淤血一直在緩慢地擴散。」
「這是一種不可逆的損傷。」
「通俗點說,她正在慢慢失明。而且,因為神經受損,她隨時可能因為顱內壓過高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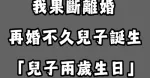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