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選擇。
是他,親手把我推開了。
是他,親手毀掉了我們之間最後一點可能。
「林殊……」他朝我走過來,向來挺直的脊背,此刻卻有些佝僂。
他伸出手,似乎想抓住我,像一個溺水的人,想要抓住最後一根浮木。
我下意識地後退了一步,避開了他的觸碰。
我們之間,隔著不過一步的距離,卻像隔著萬丈深淵。
我的疏離,讓他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他眼中的光,一點一點地暗了下去。
「對不起。」
他說。
聲音輕得像一陣風,吹過我耳邊,卻沒有在我心裡留下任何痕跡。
對不起?
多麼廉價的三個字。
如果一句對不起有用,那還要警察做什麼?
如果一句對不起,能換回我即將失去的光明,能換回我這三年所受的委屈和痛苦,我或許會考慮原諒他。
可惜,不能。
「傅司硯,」我打斷他,「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你應該道歉的對象,不是我。」
「而是那個,三年前在雨夜裡,奮不顧身救了你的林殊。」
「你把她的信任和愛,踩在腳底下,碾得粉碎。」
「你欠她的,這輩子都還不清。」
說完這些話,我感覺心裡堵著的那塊大石頭,好像終於被搬開了一些。
很輕鬆。
原來放下,是這種感覺。
我不想再看到他。
我轉身,對王醫生說:「王伯,謝謝您。我想我該走了。」
王醫生看著我們,欲言又止,最終只是點了點頭。
我沒有再看傅司硯一眼,徑直朝門口走去。
我的腳步有些虛浮。
眼前的世界又開始天旋地轉。
我知道,這是病發的徵兆。
我必須儘快離開這裡,找個地方休息。
就在我的手即將碰到門把手的時候。
身後傳來了「撲通」一聲悶響。
我回頭。
看到傅司硯,那個永遠意氣風發、不可一世的男人。
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他跪在我的面前,抬起頭,那雙曾讓我沉淪的眼睛裡布滿了血絲和絕望。
「別走。」
他祈求道:
「林殊,求你,別走。」
「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
「你想要什麼,我都給你。你想要江暖的命,我也給你。」
「只要你留下。」
他的姿態,卑微到了塵埃里。
若是三年前,我看到他這個樣子,大概會心疼得死掉吧。
可現在,我只覺得諷刺。
原來,不是他不會愛。
只是他,從來沒想過要愛我。
只有在我決定離開,在他發現自己錯得有多離譜之後,他才開始學著挽留。
可一切,都太晚了。
我的眼睛,已經快要看不見他了。
「傅司硯,」我平靜地看著他,「你站起來吧。」
「我們之間,早就結束了。」
「從你選擇相信江暖的那一刻起,就結束了。」
我轉過身,拉開了門。
身後,是他壓抑著痛苦的、野獸般的嘶吼。
我沒有回頭。
一步一步,走出了那間讓我窒息的病房。
走廊的燈光很亮,亮得有些刺眼。
我扶著牆,慢慢地走著。
眼淚,卻不爭氣地順著臉頰滑落。
原來,我還是會痛。
7
我沒有回家。
那個所謂的家,不過是傅司硯用金錢堆砌的牢籠,裡面沒有一絲一毫屬於我的氣息。
我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住了下來。
從窗戶望出去,是這個城市最繁華的夜景。
萬家燈火,流光溢彩。
可沒有一盞燈是為我而亮的。
我的視野越來越窄,眼前的世界像一個正在慢慢縮小的取景框。
我知道,留給我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手術的日期定在了一周後。
我想在這最後的時間裡,去做一些以前想做,卻沒機會做的事。
比如去海邊看一次日出。
我記得,我和傅司硯唯一一次旅行,就是去了海邊。
那是我們剛結婚時,為了應付家族的長輩,裝出來的蜜月旅行。
那幾天,他雖然依舊冷漠,但至少,沒有江暖的打擾。
我們像一對最普通的夫妻吃飯、散步、看海。
我曾天真地以為,那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沒想到,那卻是我們之間唯一的溫存。
第二天一早,我包了一輛車,去了離市區最近的海邊。
天還沒亮,海灘上空無一人。
海風帶著鹹濕的氣息,吹在臉上,有些冷。
我找了一塊礁石坐下,靜靜地等待著。
等待著,我生命中,或許是最後一次的日出。
天邊的雲層開始泛起魚肚白。
然後,是一抹淡淡的金色,在海平線上暈染開來。
再然後,一輪火紅的太陽掙脫了海與天的束縛,噴薄而出。
萬丈金光瞬間鋪滿了整個海面。
波光粼粼,壯闊又溫柔。
那一刻,我感覺自己被那片溫暖的金色包裹著。
所有的痛苦和委屈,仿佛都被這片晨光滌盪乾淨了。
我拿出手機,憑著感覺,對準了那輪日出。
我想把它拍下來。
即使以後再也看不見,我也可以憑著記憶,在腦海里反覆描繪它的樣子。
就在這時,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的鏡頭裡。
他站在不遠處,逆著光,像一個沉默的剪影。
是傅司硯。
他怎麼會在這裡?
他找到我了。
我心裡咯噔一下,下意識地收起了手機。
他朝我走了過來,每一步都走得異常沉重。
今天的他,沒有穿西裝,只穿了一件簡單的黑色風衣。
頭髮有些凌亂,下巴上也冒出了青色的胡茬。
整個人看起來憔悴又頹唐。
和我印象中那個永遠一絲不苟的傅司硯,判若兩人。
他在我身邊站定,沒有說話,只是和我一起看著遠方的日出。
海浪拍打著礁石,發出沉悶的聲響。
我們之間安靜得可怕。
最終,還是他先開了口。
「很美,不是嗎?」他的聲音沙啞得厲害。
我沒有回答。
「我查了當年的事。」他又說。
「江暖,我已經讓律師處理了。她會為她做過的事付出代價。」
「那個貨車司機,我也找到了。你給他的那筆錢,我會十倍百倍地補償他。」
他說得那麼快,那麼急,像是在急於向我證明什麼。
證明他已經知錯了,證明他正在彌補。
可這些,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江暖的下場,我不在乎。
那個司機,我幫他,也只是為了求一個心安。
我等的,從來都不是這些。
「說完了嗎?」我站起身,準備離開。
他卻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冷,還在微微發抖。
「林殊,」他看著我,眼底是濃得化不開的哀求,「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我們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我像聽到了什麼天大的笑話。
「傅司硯,」我甩開他的手,看著他,目光比海風還要冷。
「你知道,被毀掉的東西,是什麼樣的嗎?」
我指了指我的眼睛。
「就像我的眼睛,它壞了,就再也修不好了。」
「我們之間,也是一樣。」
「早就被你親手毀掉了。」
8
我的話像一把無形的刀,徹底擊碎了傅司硯最後一點希望。
他站在原地,像一座被風化的石像,一動不動。
陽光照在他蒼白的臉上,沒有帶來一絲暖意,反而更顯得他形單影隻。
我沒有再理他,轉身沿著海岸線漫無目的地走著。
沙子很軟,踩上去會留下一個個深深的腳印。
但很快,又會被湧上來的海浪撫平,不留一絲痕跡。
就像我和傅司硯的過去。
無論曾經有多深刻,最終,也都會被時間,沖刷乾淨。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直到雙腿都開始發酸,我才停下來。
我回頭望去,傅司硯還站在那塊礁石旁,像一個執拗的孩子,固執地守在那裡。
我們之間,隔著長長的海岸線,隔著翻湧的潮汐。
也隔著再也回不去的三年。
我收回視線,拿出手機,給我的律師朋友打了個電話。
我拜託她幫我辦一件事。
那就是,將我名下所有的財產,包括傅司硯給我的那一千萬,在我死後,全部捐贈給一家致力於視力障礙研究的慈善基金會。
做完這一切,我感覺自己像是卸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
了無牽掛。
剩下的時間,我想留給自己。
我回了趟老房子。
那是我父母留給我唯一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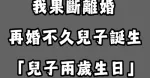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