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也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緩和了語氣:「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是,家人之間,互相幫助是應該的。錢的事你不用擔心,這個月開始,我們就AA。莉莉回來了,買菜、買營養品的錢,算作家裡的公共開銷,我們一人一半,這樣總公平了吧?」
他居然,在這個時候,又提起了AA制。
我看著他,忽然覺得無比陌生。
他嘴裡的「新觀念」,和他媽眼裡理所DANG然的「老規矩」,像兩隻手,要把我撕開。
他要求我用最傳統、最無私的方式,去為一個「大家庭」奉獻,卻要用最現代、最計較的方式,來和我這個「小家庭」的伴侶算帳。
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
「好啊。」我聽見自己說,聲音平靜得像一潭死水,「就按你說的辦。」
他以為我同意了,臉上露出了輕鬆的笑容。
他不知道,我同意的,不僅僅是AA制。
我同意的,是一場明碼標價的戰爭。
第三章 精打細算的「一家人」
莉莉和婆婆是一起來的。
建明開車去車站接的人。門一開,婆婆的大嗓門就先傳了進來:「哎喲,我的乖孫,可想死奶奶了!」
莉莉被婆婆攙扶著,臉色蠟黃,一臉倦容。建明提著大包小包跟在後面,像個盡職盡責的後勤兵。
我迎上去,擠出一點笑:「媽,莉莉,路上累了吧,快進來坐。」
婆婆把懷裡的襁褓小心翼翼地遞給我,好像我是個經過嚴格培訓的育兒嫂:「嵐嵐,快,抱抱你大侄子。這小子,路上可鬧騰了。」
我僵硬地接過那個軟軟的小東西,嬰兒身上特有的奶香味撲面而來。小傢伙睡得正熟,小嘴巴一張一合。
那一瞬間,我的心軟了一下。孩子是無辜的。
但這份柔軟,很快就被現實沖得煙消雲散。
婆婆名義上是來「幫忙」的,實際上,她就是來「監工」和「享受」的。
她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抱著孫子在客廳里溜達,嘴裡不停地指揮我:「嵐嵐,該給孩子換尿布了。」「嵐嵐,莉莉餓了,給她燉個豬蹄湯,要下奶的。」「嵐嵐,地有點髒了,你抽空拖一下。」
她自己,連一根蔥都沒切過。
莉莉呢,或許是產後激素影響,情緒很不穩定。一會兒嫌湯咸了,一會兒嫌屋裡悶了。孩子一哭,她就跟著掉眼淚,說自己命苦。
建明下了班回來,就一頭扎進次臥,陪他妹妹和外甥,說盡了好話,買各種昂貴的水果和補品。
而我,就成了這個家裡旋轉的陀螺。
早上五點半起床,給莉莉準備第一頓月子餐。然後打掃衛生,洗一家人的衣服,尤其是小山一樣的尿布。忙完這些,急匆匆地趕去開我的裁縫鋪。中午,鋪子交給臨時請的學徒,我又得跑回家做午飯。下午繼續回鋪子,傍晚關門,買菜,回家做晚飯。晚上,孩子哭鬧,莉莉和婆婆手忙腳亂,最後還是得我出馬,抱著孩子在客廳里一圈一圈地走,直到他睡著。
我像一個被上了發條的機器人,連軸轉。
而建明,他踐行「AA制」倒是很徹底。
第一周的周末,他拿著一個小本子,坐到我面前。
「嵐嵐,我們來對一下這周的帳。」
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記著每一筆開銷。
「買菜,352塊。水電費,預估80。給莉莉買的烏雞、海參,268塊。嬰兒奶粉、尿不濕,410塊……總共是1110塊。一人一半,你給我555。」
他把本子推到我面前,語氣公事公辦。
我看著那個刺眼的「555」,再看看他。他穿著乾淨的襯衫,身上還有沐浴露的清香,因為休息得好,精神飽滿。
而我呢?我穿著沾了奶漬的家居服,頭髮隨便挽著,眼下是濃重的黑眼圈。我甚至能聞到自己身上那股揮之不去的油煙和奶腥味。
我的付出,我的辛勞,我的睡眠,我的時間,在這個本子上,價值為零。
他只看得到他花出去的錢,卻看不到我投入進去的、無法用金錢衡量的一切。
「好。」我拿出手機,一分不差地把錢轉給了他。
他收到轉帳,滿意地點點頭:「這樣就清楚了,挺好的。」
是啊,挺好的。
清楚得讓我心寒。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渾身骨頭像散了架一樣疼。身邊的建明,已經發出了均勻的鼾聲。次臥里,隱約傳來孩子哼哼唧唧的聲音,和婆婆輕聲哄勸的聲音。
這個家裡,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婆婆是太后,莉莉是公主,孩子是皇太孫,建明是盡職的王爺。
而我,是那個被買來的、可以隨意使喚的丫鬟。
不,丫鬟還有月錢。
我連月錢都沒有,我甚至還要倒貼一半的開銷。
黑暗中,我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
眼淚,無聲地滑落,浸濕了枕巾。
憑什麼?
就憑我是他趙建明的妻子?就憑我是他趙莉莉的嫂子?
不,我不認。
既然你要算帳,那我們就好好算一算。
一筆一筆,都算清楚。
第四章 一張價目表

做出那個決定,其實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
那個晚上,我幾乎沒有合眼。我在想我的這八年婚姻,想我和建明從相識到相愛,想我們當初說過的那些同甘共苦的誓言。
那些誓言,言猶在耳,可說誓言的人,卻變了。
是我變了嗎?不,我還是那個願意為家庭付出,願意勤勤懇懇過日子的林嵐。
是建明變了。他被所謂的「現代觀念」洗了腦,卻只學會了對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經濟上的獨立和劃清界限。而對於家庭責任,對於丈夫對妻子的體諒和愛護,他卻選擇性地遺忘了。
他想要西方式的AA制,卻又享受著中式家庭里,妻子理所應當的奉獻。
他太貪心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床,做飯,送走去上班的建明。
然後,我沒有去我的裁縫鋪。我給學徒打了電話,讓她照看一下,說我今天有事。
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拿出了紙和筆。
我開始計算。
我的時間,我的勞動,我的專業技能(雖然只是做飯和照顧人,但那也是技能),我為此犧牲掉的裁縫鋪的收入,我被擠占的個人空間……
這些東西,怎麼量化成金錢?
很難。
但沒關係,我可以參考市場價。
我上網查了我們這個城市月嫂的平均工資,育兒嫂的收費標準,鐘點工的價錢,甚至還有私人廚師的報價。
我還查了我們這個地段,一間帶獨立衛和一間次臥的租金。
數字,一個個地被我寫在紙上。
每寫一個數字,我的心就平靜一分。
我不是在賭氣,也不是在報復。
我只是想用他聽得懂的語言,跟他對話。
既然他認為金錢是衡量一切的標準,那我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折算成金錢,擺在他面前。
讓他看一看,他所享受的這一切「免費服務」,到底價值幾何。
讓他看一看,他所謂的「公平」,到底有多麼不公平。
寫完那張「價目表」,我把它工工整整地謄抄在一張乾淨的A4紙上。
我看著上面的字,突然覺得有些可笑。
我和建明,曾經是那麼親密的愛人,如今,卻要用一張帳單來維繫關係。
這算什麼?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今天我不這麼做,那麼未來的幾十年,我可能都要活在今天這種憋屈和不甘里。
與其那樣,不如現在就撕破這層溫情脈脈的面紗。
傍晚,建明下班回來,婆婆和莉莉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孩子在搖籃里睡著了。
廚房裡,我正在燉湯。
一切看起來,都和往常一樣,風平浪靜。
晚飯時,我把那張紙,用一塊小小的冰箱貼,牢牢地貼在了冰箱門上,正對著飯桌的位置。
然後,就發生了開頭的那一幕。
建明舉著那碗雞湯,像一尊雕塑。
婆婆的臉色,由紅轉白,又由白轉青,精彩紛呈。
「林嵐!你……你瘋了!」婆婆終於反應過來,她指著那張紙,手指都在發抖,「你把我們當什麼了?我們是一家人!你居然跟自家人算錢?你的心是黑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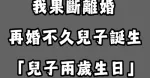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