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感到一陣煩躁。
宋巧,宋巧,又是宋巧。
一個人進入手術室的恐懼、看見病友的男友忙前忙後的羨慕、接收到視頻時的尷尬、朋友面面相覷時的難堪……還有,看見他和宋巧互動時的難過和委屈在此刻一齊涌了上來。
這些情緒化作一個略帶嘲諷的笑:「沈灼,我們已經訂婚了。」
宋巧沒有邊界感,你得有。
無論是抱著對方找擔架也好,在醫院守了對方一晚上也罷,亦或是讓對方上了副駕駛,這些都不應該。
其實我並不在意副駕駛被幾個人坐過,或者是他在工作中抱了誰。因為我理解他的一腔抱負,理解他的忙碌和不歸家,在他出任務的時候,也會整夜整夜地為他擔驚受怕。
但我沒法不在意他的態度。
我在意那個抱著宋巧衝到居民樓下,急得慌不擇路,大聲呵斥媒體「讓開」的沈灼。
我在意那個稱宋巧為「闖禍精」,實際上卻在醫院與她待了一晚上,連充電寶都沒空去借的沈灼。
我在意那個明明忙得不可開交,宋巧一聲撒嬌,就忘了還在同我通電話的沈灼。
沈灼,你的心已經偏了,你知道嗎?
4
「那又怎麼了?」
沈灼的眸子裡染上一絲不耐煩:「黎湘,只是一個副駕駛的事情,你非要小題大做,用這種審問的語氣來同我說話嗎?」
他不笑的時候,整個人氣場凌厲。
我被震懾住,感到心跳都快了幾分。
審問。
我何德何能,可以審問他?
他察覺到我的失語,壓了壓火氣,又軟言軟語地哄道:「我不是故意凶你,我忙了一整天,午飯和晚飯都沒吃,特地趕回來的,誰成想你對我這個態度……大不了以後,我不讓其他人坐副駕駛了。」
「兩個月後就是你生日,我都記著呢,那幾天我特地空出來了,你想去哪我都陪你……別計較了,嗯?」
汽車駛出地下車庫,在大路上平穩行駛。
路燈昏黃,窗外的風揚起我的頭髮。
「沈灼,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
我關上了車窗,看著自己在窗子上的倒影,說話很輕。
「這條路,我們一起走了六年。」
一開始是兩個人,四條腿,實習下班後天天走這條路回大學城。
然後是兩個軲轆的摩托車。
我總會借著抱他,偷偷摸他的腹肌。他也樂得給我摸,美其名曰「檢查訓練成果」。
再然後,就是這輛兩家父母共同支持購買的保時捷,停在地下車庫,誰想開,誰就拿去開。
房子繳了首付,是我親自盯著精裝修的。
我早就做好了與他共同生活的準備,婚期就定在來年的五一。
沈灼根本不明白,有些事情,不是他不主動,就可以規避的。
我壓下心底洶湧的情緒,決定和他說清楚。
包括流產的事。
「沈灼,我們訂婚的事情,你們整個大隊都知道,你那同門師妹宋巧不可能不知道。」
「前年情人節,我們在遊樂場排了很久的隊,她在臨上摩天輪時把你叫走;去年紀念日,我在電影院門口等你等到電影散場,事後你解釋說,宋巧的工作臨時出了紕漏,你不得不陪她一起加班……為什麼她每次都挑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出問題,難道真的有這麼多的巧合嗎?」
宋巧,我曾經很欣賞她。
同為女性,她能勇敢地選擇在懲惡揚善這條路上發光發熱——這是極少數的人能做到的事。
可是對職業的好感,構建不了複雜的人性本身。
女人天生的第六感,使我很早就察覺到她對我隱隱的敵意。
沈灼年紀輕輕就當上了隊長,長相是最符合現代審美的「中式帥哥」一類,執勤被本地的短視頻博主拍到過好幾次,當時還有 MCN 找到局裡,鬧了不少笑話。
宋巧的父親是沈灼在警校時的老師,有這一層關係,她會仰慕沈灼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但仰慕是一回事,她借著工作去滿足私慾,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現在我能當作她是年紀小、不懂事,可是如果我和沈灼結婚以後呢?
我還要忍受沈灼被臨時叫走幾次?
「我知道她父親要你照應她,可是沈灼,你畢竟是我未婚夫,應該和她說清……啊!」
沈灼一個急剎車,將車子停在街口。
「說完了?」
他的眼神冷得像冰,拉上手剎:「說完了就下車。」
「黎湘,我沈灼行得正,立得直,辛辛苦苦忙了將近半個月趕回來,不是聽你猜忌這個懷疑那個的。」
「我爸和宋叔是多年好友,我把宋巧當妹妹,我們的關係沒你想的那麼齷齪!」
「你說,我是不是太順著你了,才讓你的脾氣越來越嬌縱?」
一字一句,都像是刀子在往我心上扎。
嬌縱。
我要的並不多,怎麼就成嬌縱了?
指甲嵌進了手心的軟肉,生疼。
那張流產的病歷,就放在我隨身的包里。
我並非毫無自尊,沈灼話已至此,我明白再也沒有溝通的必要。
我果斷解開安全帶,自己下了車。
走在人行道上,餘光里看見沈灼開著車,不緊不慢地跟在我後面。
「黎湘。」
走到街尾,要過馬路,他按了兩聲喇叭,不耐煩地催促道:「上車!」
我攔了一輛計程車坐下,「師傅,去機場。」
身後保時捷的喇叭被重重按下,我沒理,關上了車門。
沈灼駕著保時捷揚長而去,車速快得捲起了路上的塵土和樹葉。
「和對象吵架啦?」司機是個大姐,本著勸和的原則寬慰我:「妹兒,有什麼事好好坐下來溝通噻,沒有什麼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嘛。」
我別過頭擦了把臉,不願讓別人看到我的狼狽:「如果真的解決不了呢?」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那就分手。」
司機大姐擲地有聲道。
5
我結束採訪後已經是凌晨,算了算時間便沒有回家,而是直接回的電視台,準備當天的早間新聞。
沈灼沒有打電話問我在哪裡,連綠泡泡消息都不曾有過。
中午我結束工作回到家,發現煙灰缸里堆滿了煙頭,屋子裡飄著一大股煙味。
沈灼在家裡抽了一晚上的煙。
我沒忍住乾嘔。
他分明知道我最討厭二手煙。
我把沙發套拆下來全洗了,往空氣里猛噴了好幾泵香水,又開了窗子通風,還是覺得不夠。
沈灼回來時沒忍住打了個噴嚏,看到新換的沙發套子陰沉了臉。
那日以後,我和沈灼默契地開始了冷戰。
我不再給他打電話,詢問他有沒有按時吃飯。
他輪休回來,我就去台里加班。
我不再關注他出的任務危不危險,不再為了他整宿整宿地睡不著覺。
起初他想同我死磕到底,偶爾打個照面,誰也不理誰。
我們之間的唯一對話,是我某天回來,往他懷裡丟了一隻唇膏。
「副駕駛撿的。」
由於上鏡的需要,我用豆沙色或裸色居多,偶爾出席正式活動,也會用正紅色的口紅。
至於橘棕色,從來都不在我的選擇範圍內。
我無意探究這支突然出現的口紅是誰掉的,又或者是故意還是無意放在那裡的。
我只是鎖上了書房的門,戴上耳機,將存檔了很久的遊戲打到通關。
沈灼出門時像是要發泄心中的不滿,把門砸得震天響。
那一刻,我決定和他提分手了。
麻煩的是,雙方父母支持購買的房子和車子的歸屬問題也要商討。
我們的工作都很忙,他忙著案子,我忙著手裡的項目,兩個人的行程碰在一起,竟然找不到一個共同的休息日。
於是,還是只能在同一個屋檐下湊合著。
半個月之後是他先服了軟。
那日我回了家,面對一大桌子琳琅滿目的飯菜陷入了沉默。
沈灼從廚房裡端出一道糖醋排骨,從牙縫裡擠出兩個字,「試試。」
「不用了,我只是回來拿東西。」
我打開衣櫃往行李箱裡面丟衣服,又從柜子里拿了一套新的水乳,「我要出差。」
台里搞了一個旅遊綜藝,姣姣她們自作主張給我報了名,美其名曰「出去放鬆」,我想了想,能公費旅遊,何樂而不為?
我合上行李箱,抬起頭看他:「我也不知道你會突然下廚,已經在台里吃過了。」
沈灼的心思其實很好猜。
他做的菜都是我平時愛吃的,做這些無非就是想同我破冰——不論是哭著喊著罵他一頓,還是撲進他的懷裡一訴衷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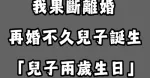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武巧輝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