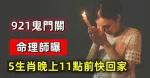救護車抵達醫院後,徐月華被迅速送入急診搶救室。醫生根據症狀立即安排了血液生化檢查、動脈血氣分析與床旁超聲。化驗結果顯示:血肌酐高達736 μmol/L,尿素氮、磷、鉀等指標嚴重升高,提示急性腎功能衰竭合併電解質紊亂;尿量顯著減少,僅有300ml/24h,同時伴有代謝性酸中毒。初步評估為糖尿病腎病基礎上進展為終末期腎衰竭(尿毒症)。醫生緊急為她安排了導尿、補液,並啟動透析程序。然而,徐月華對透析反應較差,血壓波動頻繁,心率逐日下降,未能有效改善循環穩定性。
連續5天血液透析後,她的肌酐雖有輕度下降,但尿量未恢復,意識水平逐漸減退,出現少尿性高鉀血症與心功能不全。第7日清晨,監測發現其收縮壓下降至80mmHg以下,心率不足50次/分,出現心律不齊。醫生即刻實施擴容、升壓、抗心律失常等搶救措施,並再次急查動脈血氣,提示酸中毒加重。儘管醫護人員全力搶救超過兩個小時,仍未能恢復自主心跳與呼吸。8時20分,醫院根據診斷標準宣布徐月華因終末期腎衰竭並多器官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死亡。

醫生剛從ICU病房走出,額頭還掛著未乾的汗珠,走廊盡頭,徐月華的丈夫幾乎是踉蹌著沖了上來,整個人臉色煞白,眼眶發紅,嗓子嘶啞得像被砂紙刮過:「醫生,求你告訴我,我老伴為什麼好端端的就走了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他一把攥住醫生的手腕,指節發白,聲音發顫卻越來越大,「之前不是說她恢復得挺好的嗎?血糖也穩住了,尿蛋白都下來了,醫生你當時還說,只要再堅持,腎就有希望保住……怎麼這幾天一不舒服,進醫院連兩天都沒撐住,好好的一個人就沒了啊?」
醫生聽完這些話,眉頭緩緩皺起。他沒有立刻作答,而是低聲說了句「我查一查」,便轉身回到辦公室,重新調出了徐月華入院前的檢驗數據與過去三個月的複查記錄。他一頁頁翻閱血肌酐的數值曲線、尿蛋白的變化、透析記錄表、血鉀濃度監測單……一切在入院前都未出現明顯異常。作為一名基礎腎功能受損的患者,她的指標穩定得近乎「標準模範」,飲食、運動、複診,樣樣到位。
醫生只好找來徐月華丈夫開始一點一點細查:入院前有沒有高燒?有沒有用過對腎毒性強的藥?有沒有拉肚子脫水?是不是用了草藥、營養品或者沒有如期服藥?有沒有哪一次低血糖昏厥沒說出來?坐在辦公室的徐月華丈夫,抹著眼淚,但語氣卻前所未有的清楚:「沒有,都沒有。她藥吃得很規矩,血糖儀每天記錄著。水也喝得比我還勤,血壓低就不出門曬太陽。上次醫生說綠茶能利尿,她每天早晚都喝,還天天運動。我每頓飯都是給她單獨做,油鹽和調味全是按營養師開的量,一天不多,一點不漏。」

醫生聽著這些話,只覺得胸口發堵。他反覆對照著搶救當天的記錄:短時間內電解質嚴重紊亂,血鉀高到危及心律,血壓持續下降,尿量銳減,幾乎是突然崩潰性的惡化。他緩緩闔上病歷,望著窗外沉默了很久,低聲自語:「如果連徐月華這樣配合度這麼高、生活方式都調整得這麼規範的患者……最後也擋不住腎衰的結局,那我們還能怎麼勸別人『控制就能逆轉』呢?」這句話很輕,像是說給自己聽,卻像一根鈍釘,沉沉釘進了走廊里這片長久未語的靜寂。
為了給家屬一個明確交代,主治醫生決定向院長請教——這位在腎內科紮根了三十多年的老專家,經驗極為豐富。院長接過病例後,沒有急著發言,而是沉穩地從入院記錄、既往複查、日常用藥到透析報告,一頁頁細緻翻閱,連調出的生化監測曲線都認真看了整整半小時。隨後,院長又調出發病當日的急診留觀記錄和住院前三天的用藥與體徵變化,眼神逐漸凝重起來。
隨後,院長轉過頭看向坐在角落始終沉默的徐月華丈夫,語氣平靜卻直接:「徐月華平時在喝水、運動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固定的小習慣?尤其是那種看起來很平常的。」這一問,讓在場所有人都怔住了。主治醫生略顯錯愕,似乎沒料到問題會從這個角度切入。

徐月華的丈夫一愣,隨即皺著眉回憶起來,小心翼翼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院長聽完這番話,原本緊鎖的眉頭一下舒展開了。
他點了點頭,語氣沉穩卻帶著一絲無奈:「原來如此,要知道,堅持吃藥並不意味著後顧無憂,雖然徐月華在生活上十分規律,可以說是做到了滴水不漏,但她在通過喝水、運動來控制血糖的這個期間卻忽略了三個非常低級的錯誤,因為一直被反覆忽略,才釀成了悲劇的發生!這已經不是單一事件,全國範圍內類似的病例真的太多了,我們需要反思啊!」
院長停頓片刻,聲音更加凝重:「很多人也和她一樣,覺得喝水促進代謝、運動降低胰島素敏感性,都是百利無一害的舉措,卻不知道在喝水、運動的同時還要注意這3個習慣,否則會嚴重影響腎臟的健康,甚至讓本就不堪重負的腎臟最終走向腎衰啊!而更遺憾的是,很多患者對此都毫不知情,一定要對這3個習慣引起警惕啊……」

第一個細節,是徐月華長期忽視了氣溫變化對水攝入的調節。
入秋之後,天氣逐漸轉涼,徐月華喝水的習慣並未隨之改變。她仍然像夏天干農活那樣,每天早晚各灌下一大壺水,覺得多喝水清火利尿,對身體好。可她忽略了,氣溫下降後身體出汗減少、代謝減緩,腎臟排水的負擔反而更重。特別是她習慣一次性大量飲水,常常是一頓飯後一口氣灌下三四百毫升,甚至睡前也要喝夠了才踏實。這種短時間內突增的水負荷,會導致腎小球濾過率驟然上升,使本已受損的腎單位更加疲憊。
更重要的是,徐月華飲水並未控制鈉的攝入。在農村,很多人燒水後愛加點食用堿或鹹味茶葉,徐月華泡的蓮節水中常常夾雜些鹹菜汁或藕干渣,口感雖然清淡,卻含有一定量的鈉鹽。高鈉環境會加重水鈉瀦留,誘發血壓升高和腎小管間質水腫,使腎臟微循環進一步受損。而在她腎功能臨界不穩的階段,這種無意識的水中帶鈉成為了加速腎臟惡化的隱形推手。
第二個細節,是徐月華對運動時機與強度的選擇不夠科學。
徐月華堅持早晚繞塘快走三圈,原本是個好習慣,但她選的時間點常常是早晨天色未亮、氣溫較低的時段。那段時間血壓本就容易波動,加上她常常空腹運動,體內血糖尚未完全穩定,運動後很容易誘發一過性低血糖和血流動力學變化。她常常一邊走路一邊出汗,回到家又立刻下水清洗蓮藕,冷熱交替之間,血管收縮突然,腎臟血流也跟著劇烈波動,對微血管系統造成傷害。

此外,徐月華從不監測運動後的體感變化。有時運動完後會感到疲憊、頭暈、口渴,她卻常常歸結為年紀大了正常,反而更努力加大鍛鍊強度。殊不知,在腎小球濾過功能已減退的背景下,劇烈或不適當的運動會提升蛋白尿風險,使腎臟排泄系統負擔進一步上升。尤其是在糖尿病腎病階段,運動強度必須適度穩定,否則很容易讓原本維持平衡的代償系統瞬間崩塌。
第三個細節,是徐月華習慣性地將無油少鹽理解為完全低蛋白飲食,導致營養攝入結構失衡。
為了護腎,徐月華嚴格控制菜里的油和鹽,甚至連豆腐、雞蛋都極少碰,說是怕增加腎臟負擔。她常年以藕粉、玉米糊、青菜粥為主食,午餐一碗稀飯配腌黃瓜、晚飯一碟拌藕節。雖然清淡,但幾乎沒有優質蛋白攝入。徐月華以為吃得乾淨就是對腎臟的最大保護,卻不知這類低蛋白且低能量的飲食模式容易造成營養不良,導致體內白蛋白下降、肌肉流失、免疫功能下降,使腎病進展更加迅速。
尤其是在徐月華長期勞動、血糖不穩的背景下,機體處於慢性消耗狀態,更需要足夠的優質蛋白以修復受損的組織結構。當營養供應跟不上代謝需求,身體會動用內源蛋白,從肌肉和肝臟中獲取能量,反而進一步加重氮質廢物生成,加重腎臟負擔。徐月華未意識到這一點,也從未就飲食結構進行專業諮詢,錯將吃得清當作吃得對,這一認知誤區最終成為她健康下滑的重要誘因。

 李雅惠 • 60次觀看
李雅惠 • 60次觀看

 武巧輝 • 1K次觀看
武巧輝 • 1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