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靜靜地躺在床上,身上插滿了各種各樣的管子,臉上戴著呼吸機,監護儀上跳動的數字和線條,是我唯一能確認她還活著的證據。
她的臉,比我記憶中任何時候都要蒼白,甚至帶著一絲青灰色。
我走到她床邊,輕輕地握住她的手,還是那麼冰冷。
我把她的手貼在我的臉上,滾燙的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她的手背上。
「晚晚,對不起……對不起……」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這句蒼白無力的話。
除了對不起,我不知道我還能說什麼。
語言在這樣沉重的傷害面前,顯得如此廉價。
她沒有任何反應,依舊安靜地躺著,仿佛我的懺悔,我的眼淚,都與她無關。
接下來的幾天,我寸步不離地守在ICU門口。
餓了就啃幾口麵包,渴了就喝幾口涼水,睏了就在長椅上眯一會兒。
我像一個虔誠的信徒,在贖我的罪。
我媽也一直守在那裡,她試圖跟我說話,好幾次張開嘴,最終都只是化作一聲長長的嘆息。
直到第三天,她終於忍不住了,走到我面前,聲音沙啞地說:「陳峰,你……你去吃點東西吧,別把身體熬壞了。」我抬起頭,看著她那張蒼老了十歲的臉,心中積壓了多日的憤怒、悔恨、怨恨,在這一刻,如同火山一樣,徹底爆發了。
「吃?我現在還吃得下嗎?!」我猛地站起來,雙眼赤紅地瞪著她,聲音嘶啞地咆哮著,「我老婆現在還躺在裡面生死未卜,她的子宮沒了,她以後再也不能生孩子了!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你!因為你那套狗屁不通的封建思想!因為你那句『她就是嬌氣』!
你滿意了?
你現在滿意了?!」
我的吼聲在空曠的走廊里迴蕩,引來了過往護士和病人家屬的側目。
我媽被我吼得渾身一顫,嘴唇哆嗦著,眼淚瞬間就下來了。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會這麼嚴重……我以為……我以為都那樣……」「你以為?你以為!」我一步步逼近她,情緒徹底失控,「你憑什麼以為?就憑你那些所謂的『經驗』?
你知道嗎?
醫生說,再晚半個小時,林晚就沒了!
是我,是我親手把她從鬼門關拉回來的!
也是你,親手把她推到鬼門關去的!
你不是想抱孫子嗎?
如果林晚沒了,你的孫子就沒有媽了!
你就是個殺人兇手!」
「我不是……我沒有……」我媽被我嚇得連連後退,最終跌坐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我錯了……陳峰,媽真的知道錯了……你打我吧,你罵我吧……是我害了林晚,是我害了你們啊……」看著她坐在地上老淚縱橫的樣子,我心裡的恨意,卻絲毫沒有減少,反而被一股更深的無力感所取代。
我恨她,但我更恨我自己。
如果我能早一點相信林晚,如果我能再堅定一點,如果我能不那麼懦弱……那麼,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可以避免?
可是,沒有如果。
我頹然地轉過身,背對著她,聲音冷得像冰:「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陳峰……」「我讓你走!」我再次咆哮,用盡了全身的力氣。
我媽的哭聲戛然而止。
她掙扎著從地上爬起來,看了我很久,眼神里充滿了絕望和痛苦。
最終,她佝僂著背,像一個戰敗的士兵,一步一步地,消失在走廊的盡頭。
空蕩蕩的走廊里,又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靠著牆壁,緩緩地滑坐到地上。
我沒有勝利的快感,只有無盡的空虛和絕望。
我趕走了我的母親,可我心裡的罪,卻一點也沒有減輕。
08
在ICU里待了五天之後,林晚的生命體徵終於穩定了下來,被轉到了普通病房。
她醒了。
當我再次走進病房,看到她睜著眼睛,安靜地看著天花板時,我激動得差點跪下來。
她聽到了我的腳步聲,緩緩地轉過頭來看我。
那是一雙怎樣的眼睛啊,空洞、麻木,沒有一絲光彩,像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的玻璃珠。
我們對視了整整一分鐘,誰也沒有說話。
「你來了。」最終,是她先開了口,聲音沙啞得像被砂紙磨過一樣。
「我來了。」我的聲音哽咽,「你……你感覺怎麼樣?」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是平靜地問:「孩子呢?」「孩子……孩子我送去我姐家了,我姐和我姐夫幫忙帶著,你放心,他們會照顧好他的。」「哦。」她應了一聲,又把頭轉了過去,繼續看著天花板,仿佛我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陌生人。
病房裡再次陷入了死一樣的寂靜。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做什麼。
我給她倒水,她不喝;我削了蘋果遞到她嘴邊,她緊緊地閉著嘴。
她用最殘忍的沉默,在我跟她之間,築起了一道高高的、無法逾越的牆。
醫生告訴我,她的身體恢復得不錯,但她的心理創傷,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來修復。
我知道,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我辭掉了工作,全心全意地在醫院照顧她。
我學著給她擦身,給她按摩,給她喂飯。
無論她對我多麼冷漠,我都堅持著。
我每天都會跟她說話,跟她講孩子今天又長了多少,跟她講我們以前的趣事,跟她講我對未來的規劃。
大多數時候,她都沒有任何反應。
但我不放棄。
這是我唯一的贖罪方式。
有一次,我給她讀我們以前的情書,讀到我向她求婚時寫的那一封,我的聲音忍不住哽咽了。
我抬頭看她,發現她也在流淚。
那是她醒來後,我第一次看到她哭。
我欣喜若狂,以為她終於願意原諒我了。
我放下信,握住她的手,激動地說:「晚晚,你……你是不是……」她卻抽回了手,看著我,一字一頓地說:「陳峰,你不用這樣。我不會感激你,更不會原諒你。等我出院,我們就去辦離婚手續。」我的心,瞬間從雲端跌入了谷底。
「為什麼?」我痛苦地問,「晚晚,我知道我錯了,我混蛋,我不配做你的丈夫。但是,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讓我用一輩子來補償你。」「補償?」她笑了,那笑容比哭還難看,「你怎麼補償?你還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嗎?你還給我一個子宮嗎?陳峰,你知道嗎?在搶救室里,我昏迷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很長的夢。我夢到我又回到了那個房間,我一個人躺在床上,血不停地從我身體里流出來,我好冷,好害怕,我拚命地喊你的名字,但是你沒有來。我喊你媽媽,她卻站在旁邊,指著我說,『你真嬌氣』。
那一刻,我就已經死了。
被你們,親手殺死了。」
她的聲音很輕,卻像一把重錘,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讓我痛得無法呼吸。
我終於明白,我失去的,不僅僅是她的健康,還有她對我的,那份最寶貴的信任和愛。
有些傷害,一旦造成,就再也無法彌補。
我跪在她的床邊,泣不成聲。
09

林晚的身體在一天天好轉,但她的心,依舊是一片冰封的荒原。
出院那天,陽光很好。
我為她辦好了所有手續,推著輪椅送她出去。
醫院門口,我姐抱著孩子在等我們。
幾個星期不見,小樂樂長大了不少,白白胖胖的,煞是可愛。
我姐把孩子抱到林晚面前,笑著說:「晚晚,你看,樂樂來看媽媽了。」林晚看著孩子,那雙死水般的眼睛裡,終於泛起了一絲波瀾。
她伸出顫抖的手,輕輕地撫摸著孩子的臉頰。
小樂樂似乎感覺到了媽媽的氣息,咿咿呀呀地笑了起來,還伸出小手抓住了她的手指。
那一刻,林晚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滾落下來。
她抱著孩子,把臉深深地埋在孩子的襁褓里,壓抑了許久的哭聲,終於在這一刻,徹底爆發。
她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這段時間所有的痛苦、委屈和絕望,都哭出來。
我和我姐站在旁邊,看著她,心都碎了。
我們沒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我姐家。
我媽已經被我姐送回了老家。
我姐告訴我,我媽回去後大病了一場,整天以淚洗面,嘴裡念叨的都是對不起林晚,對不起我。
我聽著,心裡五味雜陳。
在我姐家住下後,林晚的狀態好了很多。
也許是孩子的存在,給了她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
她開始吃飯,開始說話,雖然話不多,但至少不再是那副行屍走肉的樣子。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親自給孩子喂奶粉,換尿布,哄他睡覺。
看著孩子在她懷裡安睡的模樣,她的臉上,才會露出一絲難得的、溫柔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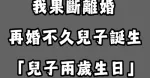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7K次觀看
武巧輝 • 7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