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來我日夜不休的照顧,我花掉的數十萬醫療費,我放棄的工作和尊嚴,全都成了一個笑話!
然而,更讓我崩潰的還在後面。
活動完筋骨的張蘭,從床墊底下摸出了那個手機,熟練地撥通了一個號碼。
因為凈化器離得近,我能清晰地聽到電話接通後,從聽筒里傳出的那個聲音。
那個我思念了整整三年,刻骨銘心,每個午夜夢回都會聽到的聲音。
「媽,他走了?」
是蘇晴!
真的是蘇晴!
她沒死!
我的世界,在這一刻,徹底崩塌了。
所有的僥倖和懷疑,都化為了殘忍的現實。
我像一個溺水的人,被這突如其來的真相徹底擊沉,連呼吸都忘了。
只聽張蘭用一種和我偷聽時一模一樣的、精明市儈的語氣說道:「走了,我看著他下樓的。這傻子,還真以為客戶找他有急事,屁顛屁顛就去了。」
電話那頭的蘇晴輕笑了一聲,那笑聲清脆悅耳,卻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在我心上反覆切割。
「他就是個傻子,不然三年前怎麼會那麼輕易就信了?骨灰盒裡裝的是什麼,他都沒懷疑過。」
「那還不是媽你厲害,找來的那個女人,身形跟你差不多,又被車撞得面目全非,誰認得出來?」
「行了,別拍馬屁了。」張蘭走到窗邊,警惕地朝樓下看了看,然後拉上了窗簾,「說正事。那個傻子昨天賺了五萬塊,我琢磨著,離我們的目標還差得遠。他爸媽那套老房子,少說也值個一兩百萬,必須想辦法讓他賣了。」
「賣房子?這可不容易。」蘇晴的語氣有些猶豫,「他雖然傻,但對他爸媽還是很孝順的。那房子是他爸媽唯一的念想了。」
「所以才要你回來啊!」張蘭的語氣變得急切起來,「只要你一出現,演一出失憶歸來的苦情戲,把他感動得稀里嘩啦,別說一套房子,就是要他的命,他都願意給!到時候,我們拿到錢,就去國外,再也沒人找得到我們。你和你男朋友,也能過上好日子了。」
男朋友……
我的腦子又被重重一擊。
原來,她不僅沒死,還已經有了新的生活,新的愛人。
而我,這個被蒙在鼓裡的「亡夫」,還在為她虛假的死亡而痛苦,為她惡毒的母親而奔波,像個小丑一樣,上演著一出自我感動的獨角戲。
我再也聽不下去了。
我關掉手機,趴在桌子上,雙肩劇烈地顫抖。
沒有眼淚,只有一種發自靈魂深處的、徹骨的寒冷。
原來,我傾盡所有去愛的女人,我掏心掏肺去守護的家庭,從頭到尾,都是一場精心編織的騙局。
他們要的,不是我的愛,不是我的照顧,只是我的錢。
從蘇晴的車禍,到張蘭的癱瘓,再到我的「仁至義盡」,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們母女倆早就寫好的劇本。
她們,把我當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傻子!
良久,我抬起頭,通紅的眼睛裡,再也沒有一絲一毫的悲傷和愛意,只剩下冰冷的、燃燒著熊熊火焰的恨意。
蘇晴,張蘭。
你們不是喜歡演戲嗎?
好,那我就陪你們,把這齣戲,演到最後。
我會親手為你們搭起最華麗的舞台,然後,再讓你們從最高處,狠狠地摔下來,摔得粉身碎骨!
04
接下來的幾天,我表現得一如往常,甚至比以前更加「盡心盡力」。
我不再只是機械地完成照顧岳母的日常任務,而是開始主動地和她「交流」。
我會坐在她的床邊,一邊給她按摩,一邊絮絮叨叨地講著我和蘇晴過去的甜蜜往事。
「媽,您還記得嗎?我和蘇晴第一次見面,是在大學的圖書館。當時她穿著一條白色的連衣裙,陽光灑在她身上,就像個天使。我當時就看呆了,覺得這輩子非她不娶。」
「還有我們結婚的時候,您拉著我的手,說蘇晴這孩子從小被我們慣壞了,讓我多擔待。您放心,我一直記著呢。蘇晴是我的妻子,我愛她,照顧您,都是我應該做的。」
每當我說起這些,張蘭的眼中都會適時地流露出一絲「感動」和「悲傷」的微光,喉嚨里發出幾聲意義不明的嗚咽。
而我,則通過手機螢幕,冷冷地欣賞著她拙劣的演技,心中沒有絲毫波瀾。
我在等,等一個合適的時機,把我精心準備的「誘餌」拋出去。
終於,在一個周末的下午,機會來了。
我「無意」中把手機落在了張蘭的床頭柜上,然後藉口下樓扔垃圾,躲在樓梯間裡,用另一部備用手機撥通了自己的號碼。
電話響了很久才被接通,我沒有說話。
我知道,張蘭一定會接,她會以為是我忘了什麼事,去而復返。
果然,我聽到電話那頭傳來張蘭小心翼翼的呼吸聲。
時機到了。
我立刻掛斷電話,然後用備用手機撥通了我一個發小的號碼。
電話一接通,我就用一種極度興奮又刻意壓低的語氣說道:「阿強!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爸媽那套老房子,終於要拆遷了!」
我知道,張眾一定在聽。
她對那套房子,已經覬覦很久了。
發小被我搞得一頭霧水:「拆遷?你家那破地方?我怎麼沒聽說?」
「我也是剛得到的消息,內部文件,還沒公布呢!」我繼續「神秘」地說道,「據說開發商給的補償款很高,按面積算,我家那套六十平的房子,至少能賠兩百五十萬!」
「臥槽!真的假的?那你小子不是發了?」發小的聲音也激動起來。
「噓!你小點聲!」我裝作緊張地看了看四周,「這事兒你可千萬別往外說。我還沒想好怎麼跟我爸媽開口。你知道的,他們對那套老房子有感情。」
「那你打算怎麼辦?」
「還能怎麼辦?」我嘆了口氣,語氣變得沉重起來,「我岳母這病,你也知道,就是個無底洞。前兩天醫生又說了,國外有一種新的幹細胞療法,效果很好,但一個療程就要一百多萬。我正愁錢呢,這筆拆遷款,簡直就是救命錢啊!」
我故意把「救命錢」三個字說得特別重。
「我打算先斬後奏,拿到錢,立刻給我岳母安排治療。等她病好了,我再跟我爸媽負荊請罪去。他們就算生氣,看在一條人命的份上,應該也能理解我。」
說完,我沒等發小再說什麼,就匆匆掛斷了電話。
我知道,我的這番表演,已經通過那部沒有掛斷的手機,一字不落地傳到了張蘭的耳朵里。
兩百五十萬的拆遷款。
足以讓任何一個貪婪的人,徹底瘋狂。
我回到樓上,張蘭依然躺在床上,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但我從監控里看到,就在我上樓的時候,她立刻抓起手機,編輯了一條簡訊飛快地發了出去。
魚兒,已經咬鉤了。
接下來的幾天,我明顯感覺到張蘭有些「急」了。
她會「不經意」地向我打聽「拆遷」的事情,雖然話說得含糊,但我能聽出她語氣里的迫切。
我則表現得一臉愁容,告訴她,我爸媽那邊思想工作很難做,他們死活不同意,覺得房子是他們的根,不能賣。
「媽,您別急,我再想想辦法。就算求,我也要求我爸媽同意。您的病,不能再拖了!」我握著她的手,說得情真意切,眼眶都紅了。
監控畫面里,我走後,她立刻撥通了蘇晴的電話,語氣暴躁地把情況說了一遍。
「……這個死老頭老太太,真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這時候礙事!」
「……不行,不能再等了!夜長夢多!你那邊準備得怎麼樣了?必須儘快回來!只有你回來,才能徹底套牢那個傻子,讓他心甘情願地把錢交出來!」
電話那頭的蘇晴沉默了片刻,然後用一種下了很大決心的語氣說:「好,媽,我知道了。你再穩住他幾天,我下周就回去。」
聽到這句話,我笑了。
我的網,終於要收緊了。
我開始為蘇晴的「回歸」做準備。
但這準備,不是迎接一個失而復得的愛人,而是為一個即將落入陷阱的獵物,布置好最後的刑場。
我聯繫了律師,一個我大學時的同學,他最擅長的就是打經濟詐騙類的官司。
我把所有的錄音和視頻證據都給了他一份,他看完後,震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只拍著我的肩膀說了一句:「兄弟,放心,這事兒交給我。不讓她們牢底坐穿,我名字倒過來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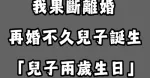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7K次觀看
武巧輝 • 7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