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問她那個「你」到底是誰!
可是,理智的最後一根弦死死地拉住了我。
衝上去質問?
然後呢?
她會承認嗎?
她只會繼續裝作那個癱瘓的可憐老人,用眼淚和無辜來博取同情,甚至會反咬一口,說我因為照顧她壓力太大,精神失常,出現了幻覺。
而我呢?
我沒有任何證據。
單憑一段沒頭沒尾的偷聽,誰會相信我?
在所有鄰居、朋友的眼裡,我是一個孝順的女婿,她是一個可憐的老人。
我的指控,只會被當成一個笑話,一個農夫與蛇的現代版鬧劇,而我,就是那個忘恩負義的農夫。
不,我不能就這麼算了。
如果這真是一場騙局,那它的策劃者絕不可能只有張蘭一個癱瘓在床的老人。
她的背後,一定還有人。
那個她打電話的對象,那個她等著「回來」的人,是誰?
我的腦海中閃過無數張面孔,蘇晴的親戚,她們家的朋友……但都被我一一否決。
突然,那個最不可能,也最讓我恐懼的念頭再次浮現出來。
蘇晴……
不,不可能!
我親眼看到她被推進火化爐,我親手將她的骨灰盒下葬。
她已經死了,死得透透的了!
我狠狠地給了自己一巴掌,試圖用疼痛讓自己清醒。
一定是我想多了,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死而復生的事情?
可是,除了她,還有誰能讓張蘭如此處心積慮?
還有誰,值得她們母女倆布下這麼大一個局,來騙取我的一切?
我的心亂如麻。
不行,我必須冷靜下來。
在沒有拿到確鑿的證據之前,我絕不能打草驚蛇。
從今天起,我要把這場戲繼續演下去。
我要當一個比她們更出色的演員。
我從花壇邊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被風吹亂的衣服,走進旁邊的一家便利店,買了一包煙和一瓶冰水。
我很少抽煙,但此刻,我迫切需要尼古丁來麻痹自己即將崩潰的神經。
我回到樓上,掏出鑰匙,故意弄出很大的聲響,然後像往常一樣打開門,喊道:「媽,我回來了。今天有點堵車,耽誤了。」
臥室里傳來張蘭含糊的「嗯」聲,聽起來和我離開時沒有任何區別。
我走進她的房間,她正躺在床上,眼神呆滯地望著天花板,仿佛剛才那通電話,那個精明算計的婦人,都只是我的幻覺。
如果不是親耳聽見,我絕對無法把眼前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和騙子聯繫在一起。
她的演技,真是爐火純青。
我的心裡冷笑,臉上卻堆起了關切的笑容:「媽,餓了吧?我買了您最愛吃的餛飩,這就去給您熱熱。」
她沒有說話,只是眼珠子動了動。
我像往常一樣,給她喂飯,給她擦臉,給她按摩僵硬的四肢。
我的動作依然輕柔,我的語氣依然溫和,但我知道,有什麼東西已經徹底不一樣了。
每一次觸碰她的皮膚,我都感到一陣生理性的噁心。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在照顧一個可憐的長輩,現在我才知道,我是在伺候一個將我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惡魔。
晚上,我躺在床上,毫無睡意。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憶著這三年來的一點一滴,試圖從中找出一些被我忽略的蛛絲馬跡。
我想起來了,蘇晴出車禍時,現場非常慘烈,她的面部被嚴重毀壞,幾乎無法辨認。
當時我悲痛欲絕,根本沒有仔細看,只憑著她身上的衣服和那枚我送她的戒指就確認了身份。
現在想來,這會不會是一個漏洞?
還有張蘭,醫生說她是心病,可這三年來,我請了最好的專家,用了最好的藥,她的情況卻絲毫沒有好轉。
是不是從一開始,她就沒病,所以才「治不好」?
我還想起,大概一年前,我無意中看到張蘭的手機帳單,發現有一個號碼的通話頻率異常地高。
我當時問她,她含糊地說是一個遠房親戚,關心她的病情。
我信了,甚至還覺得這個親戚有情有義。
現在想來,那個號碼,會不會就是今天下午她通話的那個?
一個個疑點,像拼圖一樣,在我腦海里慢慢拼接,一個可怕的真相輪廓,漸漸清晰起來。
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須立刻行動。
第二天一早,我藉口說要去見一個客戶,離開了家。
但我沒有去任何地方,而是直奔電子城。
我要買一個東西,一個能揭開所有真相的東西——一個針孔攝像頭。
我要親眼看看,在我離開家之後,這個「癱瘓」的岳母,到底在做些什麼。
我要親耳聽聽,她到底在和誰通話,謀划著怎樣惡毒的陰謀。
我要把她們的罪證,一點一點地,全部記錄下來!
03

電子城裡魚龍混雜,我找了一家看起來最不起眼的店鋪走了進去。
老闆是個精瘦的中年男人,見我東張西望,便主動上前搭話。
我壓低聲音,說出了我的需求。
老闆心領神會地笑了笑,把我帶到裡屋,從一個上鎖的柜子里拿出幾個偽裝成各種日常用品的攝像頭。
有偽裝成插座的,有偽裝成煙霧報警器的,還有偽裝成綠植裝飾的。
我最終選擇了一個偽裝成空氣凈化器的。
它體積不大,放在臥室里不會顯得突兀,而且自帶錄音和夜視功能,可以通過手機APP實時監控。
付了錢,我把東西裝進背包,像做賊一樣迅速離開了電子城。
回到家,張蘭依然癱在床上,對我今天的「反常」外出沒有表現出任何異樣。
我心中冷笑,她大概巴不得我天天出去跑業務,這樣才方便她自由活動。
我捧著新買的空氣凈化器走進她的房間,臉上堆著殷勤的笑容:「媽,最近天氣干,我看您總咳嗽,給您買了台新的空氣凈化器,帶加濕功能的,對您身體好。」
張蘭渾濁的眼睛看了看我手裡的機器,含糊不清地說了句:「又……亂花錢……」
「錢花了還能再賺,您的身體最重要。」我一邊說著,一邊不動聲色地尋找最佳的安裝位置。
最終,我把它放在了正對著床的床頭柜上。
這個角度,可以將整個房間的情況一覽無餘,而且離床很近,錄音效果也會是最好的。
我熟練地插上電源,連接Wi-Fi,然後在手機上打開監控APP。
清晰的畫面立刻出現在螢幕上,張蘭那張衰老而虛弱的臉,被鏡頭捕捉得一清二楚。
很好,魚餌已經放下,現在就等魚兒上鉤了。
為了給張蘭創造「表演」的機會,我特意在第二天對她說,前兩天那個項目,客戶那邊發現了一點小問題,需要我回公司和同事一起緊急處理,可能要待一整天。
「去吧……工作……要緊……」她一如既往地「善解人意」。
我拎著電腦包出了門,卻沒有走遠,而是拐進了小區對面的一個咖啡館,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
我點了一杯咖啡,拿出手機,點開了那個隱蔽的監控軟體。
畫面里,張蘭的房間一片寂靜。
她就那麼靜靜地躺著,一動不動,和我離開時沒有任何區別。
一分鐘,兩分鐘……十分鐘過去了,她還是保持著那個姿勢。
我開始有些懷疑,難道昨天真的是我精神恍惚,產生了幻覺?
就在我耐心快要耗盡的時候,畫面里的人,突然動了!
我看到她先是小心翼翼地側了側頭,似乎在傾聽外面的動靜。
在確認我真的離開,並且周圍沒有任何異常之後,她……竟然緩緩地,從床上坐了起來!
我的心跳瞬間漏了一拍,死死地盯著螢幕,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只見她先是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活動了一下似乎有些僵硬的脖子和肩膀,那舒展的姿態,哪裡有半分癱瘓病人的樣子?
接著,她掀開被子,利落地翻身下床,穩穩地站在了地板上!
她不僅站了起來,還原地做了幾個伸展運動,踢了踢腿,扭了扭腰,動作流暢,身手矯健,比公園裡晨練的大爺大媽還要靈活!
這一幕,對我造成的衝擊,不亞於親眼看到死人復活。
我的大腦「嗡」的一聲,一片空白。
憤怒、震驚、荒謬……種種情緒交織在一起,讓我幾乎要捏碎手中的手機。
癱瘓了三年的人,就這麼站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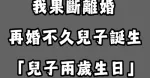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7K次觀看
武巧輝 • 7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