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了,我一直活在謊言里。
我以為自己是情深義重的典範,為了亡妻的遺願,心甘情願地伺候癱瘓的岳母,散盡家財,耗盡心力。
我以為這是愛與責任的延續。
直到那天,我提前回家,門虛掩著,岳母的房間裡傳來那句足以將我靈魂碾碎的話語:「他已經上鉤了,你什麼時候回來?」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不是什麼聖人,我只是一頭被精心圈養,等待宰殺的豬。

01
「小林啊,媽想喝口水。」
張蘭,我那癱瘓在床的岳母,用她一貫虛弱又帶著點歉意的聲音喊我。
我立刻放下手中正在敲打的鍵盤,快步從書房走到她的臥室。
這間朝南的屋子,是整個家裡採光最好的,三年前,妻子蘇晴剛走,我就把母親從她陰暗的小房間裡搬了出來,只為讓她能多曬曬太陽。
「媽,來了。」我熟練地拿起水杯,將吸管湊到她嘴邊,另一隻手小心翼翼地托著她的後腦。
她費力地吸了兩口,渾濁的眼睛裡流露出一絲滿足。
「辛苦你了,小林。我們家蘇晴……是我們家對不起你。」張蘭又開始念叨這句重複了三年的話。
我笑了笑,掩去眼底的疲憊,柔聲說:「媽,說這些幹什麼,我們是一家人。照顧您是應該的。」
三年前,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帶走了我的妻子蘇晴。
我至今都記得那天,天是灰的,雨是冷的,醫院的白色床單上那抹刺目的紅,成了我永恆的噩夢。
蘇晴的離去,對我而言是天塌了。
而對於她的母親張蘭,則是精神和身體的雙重垮塌。
在蘇晴的葬禮上,她哭得暈厥過去,醒來後,就全身癱瘓,失去了行動能力,連話都說不清楚。
醫生說,這是急性應激障礙導致的轉化症,俗稱「心病」。
病根在心裡,什麼時候能好,誰也說不準。
所有人都勸我,說我仁至義盡了,一個毫無血緣關係的老人,沒道理讓我一個年輕人搭上一輩子去照顧。
我的父母更是氣得和我斷絕了關係,他們罵我是個傻子,為了一個外人,連自己的親生父母都不要了。
但我做不到。
我忘不了蘇捨身救我的那一幕,如果不是她推開我,現在躺在冰冷墓碑下的就是我。
我也忘不了她臨終前,拉著我的手,斷斷續續地說:「林……林風……照顧……我媽……」
為了這個承諾,我辭去了前途大好的程式設計師工作,靠著以前接私活攢下的人脈,在家做一些零散的項目,這樣才能全天候地照顧岳母。
一日三餐,擦身換洗,按摩理療,我學得比護工還要專業。
蘇晴走後留下的積蓄,加上我的收入,幾乎全都砸進了岳母高昂的治療和康復費用里。
鄰居們都誇我是「當代二十四孝女婿」,說蘇晴在天有靈,也該安息了。
每當這時,我都會擠出一個苦澀的笑容。
他們不懂,我做的這一切,不為名聲,只為心安,為了對得起那個用生命愛過我的女人。
今天,我接的一個項目到了最後交付階段,客戶催得急,我不得不熬個通宵。
一直忙到下午三點,總算把所有代碼都調試完畢,成功交差。
客戶很滿意,立刻把尾款打了過來。
看著銀行帳戶里多出的五萬塊錢,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這筆錢,又能支撐岳母兩個月的開銷了。
我關掉電腦,起身活動了一下僵硬的脖子,準備去給岳母做點吃的。
可剛走到客廳,就發現錢包和鑰匙都忘在了公司。
昨天去公司拷貝項目資料,走得匆忙,竟然落下了。
我拍了拍腦袋,岳母的藥快吃完了,下午得去醫院開,沒鑰匙可不行。
我跟床上的岳母打了聲招呼,說我出去一趟,很快回來。
她含糊地應了一聲,眼神一如既往地空洞。
從公司拿回東西,比我預想的要快,來回只用了不到四十分鐘。
我掏出鑰匙,正準備開門,卻發現門只是虛掩著,露出一條縫。
我心裡「咯噔」一下,難道是進賊了?
我屏住呼吸,悄悄推開門,側耳傾聽。
屋子裡很安靜,沒有搏鬥的痕跡,也沒有被翻亂的跡象。
我稍微鬆了口氣,或許是早上出門時風把門吹開了。
正當我準備換鞋時,岳母的房間裡,卻突然傳來了一陣清晰的、壓低了的說話聲。
那聲音……是岳母的!
可是,不對!
絕對不對!
岳母因為癱瘓,聲帶也受到了影響,說話向來是含糊不清,斷斷續續的。
可此刻,從門縫裡傳出的那個聲音,雖然刻意壓低了,但卻中氣十足,吐字清晰,甚至還帶著一絲按捺不住的興奮和算計。
我的血液瞬間凝固了,手腳冰涼,像一尊雕塑般僵在原地。
「……放心吧,都按計劃進行著呢。他那個人,死心眼,重感情,最好拿捏了。」
是岳母的聲音!
千真萬確!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心臟狂跳,幾乎要從胸腔里蹦出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難道是我幻聽了?
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一步一步,像做賊一樣,悄無聲息地挪到岳母的房門前。
我不敢靠得太近,只能通過那道門縫,緊張地向里窺探。
房間裡,岳母依然躺在床上,姿勢和我離開時一模一樣。
但她的手裡,卻握著一個手機,正貼在耳邊。
她的臉上,哪裡還有半分平日裡的呆滯和虛弱?
那雙渾濁的眼睛裡,此刻閃爍著精明算計的光芒,嘴角勾起一抹我從未見過的、帶著嘲諷和得意的笑容。
我的心,一瞬間沉入了谷底。
只聽她繼續對著電話那頭說道:「他剛接了個大單,賺了五萬,我親耳聽到的。這還不夠,他爸媽不是還有套老房子嗎?我得想辦法讓他把那套房子也賣了,給我『治病』。」
電話那頭似乎說了些什麼。
岳母冷笑一聲,語氣里充滿了不屑:「他?他已經被我那個死鬼女兒迷得神魂顛倒了,到現在還對她念念不忘呢。我只要天天在他面前念叨我女兒的好,再裝裝可憐,他就什麼都願意給我。這三年,他哪次不是我說東,他不敢往西?」
「死鬼女兒」……這四個字像四根燒紅的鋼針,狠狠地扎進了我的心臟。
蘇晴是她的親生女兒啊!
她怎麼能用這麼惡毒的詞彙來形容?
我的身體開始不受控制地顫抖,一股寒意從腳底直衝天靈蓋。
「行了,不說這個了。」岳母的語氣變得有些不耐煩,但隨即又轉換成一種近乎諂媚的期待,「最關鍵的是,他已經上鉤了,所有的積蓄都投進來了。現在網撒得差不多了,你……什麼時候回來?」
「轟——」
最後那句話,如同九天驚雷,在我腦海里炸響。
他已經上鉤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
回來?
誰回來?
一個癱瘓在床的老人,在等誰回來?
一個荒謬、可怕、卻又似乎唯一合理的念頭,瘋了一樣地從我心底最深處鑽了出來。
我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不讓自己發出任何聲音。
牙齒因為過度用力,咬得嘴唇滲出了血絲,一股鐵鏽味在口腔里瀰漫開來。
我看著房間裡那個熟悉又陌生的女人,看著她臉上那得意的、貪婪的笑容,只覺得渾身的血液都逆流了。
三年的付出,三年的犧牲,三年的自我感動……原來,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
而我,就是那個最可笑、最愚蠢的獵物。
02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離開那道門縫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魂不守舍地退回到玄關,再輕輕帶上門的。
我像一個被抽走了靈魂的木偶,機械地轉身下樓,整個世界都在旋轉,耳邊只剩下岳母那句「他已經上ষেধ了,你什麼時候回來」在瘋狂迴響。
我在樓下小區的花壇邊坐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夜幕降臨,華燈初上。
深秋的冷風吹透了我單薄的衣衫,但我感覺不到冷,我的心比這風、比這夜還要冷。
憤怒、背叛、屈辱、噁心……無數種情緒在我胸中翻江倒海,幾乎要將我撕裂。
我恨不得立刻衝上樓去,當面撕開張蘭那張偽善的嘴臉,質問她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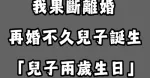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7K次觀看
武巧輝 • 7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楓葉飛 • 4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