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再是那個咄咄逼人、斤斤計較的潑婦,只是一個失去了母親,又發現自己錯得離譜的女兒。
陳建軍站在那裡,像一尊雕塑。他手裡的信紙,已經被淚水浸透。良久,他緩緩地轉過身,看著我。
他的眼睛裡,充滿了深深的愧疚和痛苦。
他張了張嘴,喉結滾動,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最後,他抬起手,狠狠地給了自己一個耳光。
「啪」的一聲,清脆響亮。
「小舒……對不起。」他聲音沙啞,充滿了無盡的悔意,「我……我不是人。」
我看著他,看著痛哭流涕的陳建紅,再看看懷裡被嚇到的兒子,我的心,像被一隻手緊緊地揪住,又酸又疼。
原來,婆婆什麼都知道。
她知道我的付出,知道我的委屈,也知道我心裡的苦。
她只是不善於表達。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最笨拙,也最真誠的方式,給了我最大的肯定和補償。
而我,卻因為自己的猜忌和怨恨,差點毀了這個家。
我抱著兒子,眼淚也無聲地流了下來。這一刻,我不是為自己哭,而是為那個已經離去,卻用一封信守護了這個家的老人而哭。
那一晚,我們三個人,誰也沒有再提錢的事。
陳建紅哭累了,眼睛腫得像核桃。她走到我面前,低著頭,聲音嘶啞地說:「嫂子……對不起。是我……是我混蛋,是我小心眼,是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咱媽。」
我搖搖頭,扶住她:「別說了,都過去了。」
是啊,都過去了。
當婆婆的信被讀出來的那一刻,所有的怨恨,都煙消雲散了。
陳建軍默默地收拾了茶几上的狼藉,然後走進廚房,給我們下了一鍋熱氣騰騰的麵條,臥了三個荷包蛋。
我們三個人坐在餐桌前,默默地吃著面。
誰也沒有說話,但彼此之間那道看不見的牆,已經消失了。
第二天,陳建紅一大早就走了。走之前,她把她的那份,十萬塊錢,留在了桌上。她給我發了條信息,說:「嫂子,這錢我不能要。媽說得對,這個家,你付出得最多。錢你拿著,給陳晨好好讀書。以後,我會常回來看你們的。」
我看著那筆錢,心裡百感交集。
我把錢給陳建軍,讓他轉回去。
「建紅的日子也不好過,這是媽給她的,她應該拿著。」我說。
陳建軍看著我,點了點頭。
他走過來,從背後輕輕地抱住我,把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
「小舒,謝謝你。」他輕聲說,「也對不起。」
我靠在他懷裡,搖了搖頭。
經過這件事,我們都成長了。
那本四十二萬六千七百塊的存摺,最終,我們按照婆婆的遺願,重新做了分配。
陳建紅的那十萬,我們堅持給了她。陳建軍的那一份,我們存了起來,作為家庭的緊急備用金。
剩下的二十二萬多,我沒有像婆婆說的那樣,全部留給自己。我拿出了一大部分,以婆婆的名義,給兒子陳晨辦了一個教育基金。
我只給自己留下了一小部分。
我用這筆錢,給自己報了一個一直想學的會計資格證的培訓班。我不想再做全職主婦了,我想重新回到職場,找回那個曾經自信、獨立的自己。
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陳建軍時,他沒有絲毫猶豫,全力支持我。
「去吧,」他說,「家裡有我。以後,換我來支持你。」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從前,但又好像什麼都不一樣了。
家裡還是那個家,人還是那些人,但我們彼此之間的心,卻貼得更近了。
我時常會想起婆婆,想起她那張總是沒什麼表情的臉。我現在才明白,在那張平靜的面孔下,藏著多麼深沉而細膩的愛。
她不善言辭,卻把所有的愛,都寫進了那封信里,刻進了那本存摺里。
她用她一生的積蓄,給我們這些晚輩,上了最重要的一課。
錢,很重要。但比錢更重要的,是家人的理解、信任和愛。
那是一個周末的下午,陽光很好。我坐在陽台的藤椅上看書,陳建軍在廚房裡笨拙地學著做紅燒肉,鍋碗瓢盆的聲音叮噹作響。兒子陳晨在客廳的地板上,專注地拼著樂高。
我抬頭,看著眼前這幅景象,心裡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和安寧。
那個曾經讓我感到窒息的家,此刻,充滿了溫暖的煙火氣。
我想,這大概就是婆婆最想看到的樣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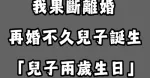
 武巧輝 • 4K次觀看
武巧輝 • 4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